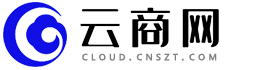人物金士杰:演员应该平凡一点
演员都是先做人,然后才是演戏。
“我从来没有答应在外头接戏接那么久,两个多月在上海,一个人。一般,我都只接那种短期的,可以回家看家人陪孩子,我是一个父亲。演员都先要做人,然后才是演戏。”
“过两天我老婆孩子就要来了,我太开心了。”
这是昨天下午3点半,和金士杰坐在兴国宾馆咖啡厅里。在金士杰眼中,看到了开心的光。人开心的瞬间,眼神里的光会闪烁,特别打动人,就好像他在话剧《父亲》里扮演的安德烈,时不时也有这样闪烁的光,就算观众坐在二楼包厢也能看得清清楚楚。
1 父亲是否是很被压抑,很没有话语权的一个人?
全世界大部分的爸爸,包括我自己在内,在家里都比较没有话语权。妈妈和小孩子吃喝在一起,没有包袱,打在一起,笑在一起,甚至身体的接触等等。但是父亲大都就是在旁边,他们提供了一些知识,提供了一些理性的对话。

父亲很保守,很多父亲可能在家里是被冷落的,他都不知道怎么跟孩子拥抱。他们习惯保持一种距离,一种家长的姿势。他们和孩子牵个手,碰一下身体都不自然。我也对我的父亲很有感情,但我也看见身为父亲难以跨越的某种界限。我想跨越它。
2 在《父亲》的父亲身上,找到上路的感觉吗?
我是江湖上很有名的客串大王,没事就串一下戏。这也需要运气,刚好有这么片漂亮的绿叶。并不是每张绿叶都写得这么出色,或者是你跟那个绿叶的关系,不见得一下子就那么容易融合。需要刚好跟那个角色的缘分到了,和导演的沟通,对那个故事的一种领悟,对那个台词背后的一些感情摸索都很舒服的话,就比较容易上路。但必须承认,某些时候我也会迷路,也有的时候比较高兴,好像上路了。
金士杰给晚报读者的签名
这个问题问的时间点很好,因为前两天,我可能还讲不清楚。
这部戏对很多观众来说是一种挑战。一般老百姓应该都会站在人之常情去关注老人,想到自己的经历,和病床上的亲人的一些故事,或者更多的是,他会想,将来有一天我也会这样。但是我对这出戏的理解不在这里。我不会把社会公益或者大众情感,作为我要表达的首要任务。我关注的是有没有一个人写出了一个好故事,写出了一个好角色,好到我想把那个人演出来,这是我唯一的工作。
我如何面对那个人?如何演绎一个不能称之为好人的人——甚至可以说是承载着“不可原谅之恶”的人?这就是我为什么极度迷恋我的工作,那是我追求的。如果今天写的是一个多么讨人喜欢的可爱小老头人,那就不是安德烈,我可能也不见得会点头来演出。有时候,别人反对的东西刚好是我以为最好的东西。
在创作来讲,那是极有趣的事情,那是推动创作者想去叩门,想去一窥究竟的东西。创作者是来讨我们高兴的人吗?一个游乐园的安排者吗?当然不是。我们要和创作者一起走进难以下定义的一个世界,那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。
角色复杂,才值得观众来看,才值得创作者去写,值得演员去演。对我来讲,安德烈确实是这样的一个角色。我今天还把剧本又拿出来翻,我感觉有些句子,我应该还要说得再“恶”一点。
人是什么?人和人的关系会有怎样的留白?我所饰演的这个角色的戏,可能会让人们对这个问题,在每个晚上都会有微微不同的感悟和理解。
3 因为不会饶过自己,是否有代价?
大陆观众最先认识我的一个角色,或许就是在电影里扮演舒淇的父亲,那段5分钟的独白。那个时候,我心中有一个决心,决心来自于我对于“父亲”这个概念的理解,我觉得我要替天下有大龄女儿的父亲说出心声——父亲的爱是什么,我要向她们说出来。
电影里只有5分钟,但是我准备了两个月,我在家里读了很久,每天都在揣摩应该是怎样的情绪,怎样的内心感受。重点是我没有饶过自己,周围人很快就觉得可以了,我自己就一直觉得不及格。那么多的句子是台词,不是生活的话语,我找不到语言的动机,只看到优美的台词。这个事情我过不了关,这是我在表演上的一种坚持。第一天上表演课,我的老师就告诉我,永远不要上台说台词,天底下没有台词这个事情。人就要说人话。我要做到把我百分之两百的力气放上去,感觉我不会轻易要再改动一下,好像面对一幅已经完成的画。
不能饶过自己的代价,就是你最后需要时间从那个角色里面出来。安德烈在最后一场,趴在护工怀里嚎啕大哭,像个孩子。那一刻,他所有已知的身份、过往、关系,都坍塌了。他“回归”到新生儿时的那种啼哭,那种极度渴望母亲怀抱的叫嚣式的啼哭……
所以,我没有办法谢幕,真的没办法。我已经跟观众道别了,我在剧中完美地做了一个漂亮的结束,现在要我跑出来跟大家眉飞色舞地说“哈啰”,那我不是打自己巴掌吗?我只能消失。
我们为什么到剧场,剧场最初是举行祭祀的地方,从某种意义上来讲,就是让大家在看戏的这段时间里,共同完成某种进化。
我们应该尊重身体自然的节奏,不要刻意,不要急于脱离苦海,急于扭改身体自然的节奏,应该顺势。我们不需要借狂欢,借放肆,或者拥抱,或者是什么东西掩饰我们的悲伤或者是分离。就像如果今天参加完一个葬礼,我不需要急于去喝大酒,去跟人家寻欢作乐。我该安静就安静,如果我有点消沉,我就让自己有点消沉,只要不犯错就好。
演员在台上总是一下跳进、一下跳出某个情绪,老在疯狂边缘跑,久而久之,好像我们就会有一个很戏剧性的人格。但演员就是普通人,我心中很希望每个演员都能够平凡一点。
4 这部戏需要怎样的观赏基础?
这个基础名为“主观”。
我认为扮演安娜的演员,天底下任何演安娜的那个人,下戏后,她的痛苦会远超过安德烈。在剧中,她一直在压抑,一直过不了关,并且还亲手把钉子钉在她父亲的手上。她亲手签了父亲的卖身契,她的日子会好过吗?从某一个角度来看,安德烈有一个狡辩人格上的变化。他的健忘,他在某一瞬间,他会忘记前一个时刻,当他抱着那个女护工的时候,在那个当下,他心里的地狱之火灭了,仿佛进入天堂——好像在温柔而无边的草原上,傻傻吹风……
但我们不能替这样的病人代言,我们没有办法得知他们对于记忆这件事情是不是彻彻底底地抹掉了,他们残留了多少个体的记忆?受苦,受累,挣扎,面对这样一个要躺在床上很久很久的人,我就很心疼。
这个故事的魅力,都建立在“主观”上。你以为是安德烈的主观,后来发现那是作者陪着安德烈的主观,再往下看,这个客观世界也乱了。它有着折射之后的再折射——那个世界的记忆非常漂亮,以至于那一巴掌打到我们身上,我们都不知道应该先摸脸还是其他什么地方。初次阅读这个剧本的时候,我对导演蒋维国说,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有商业魅力的戏。这是一个很小众的,有一点酷的小剧场。这不是一个让大家来拥抱温情,回忆过往,充满家庭温暖的戏。甚至,它是有点冷血的……
5 最初就想做演员吗?
我入行的第一秒钟,就决定我这一辈子不是来干演员的,而是编!导!演!从我起步的时候,在剧团成立的第一天,我只做主动者,不做被动者。几乎一直是这样。后来剧团解散了,我才从舞台圈来到影视圈。后来又要面对一些现实,娶老婆生孩子之后,我开始出来赚点奶粉钱。但我不接长戏,只接短戏,然后我还挑,有的时候是这个钱不错;有的时候是这个剧本的质感不错;有的时候是因为我跟谁的关系不错;可以说各有所图吧,所以我一直觉得我还活得蛮狡猾的。而且我也没有那么贪心,没有那么强烈的物质欲望或者对自己的要求,也没有那么不得了。但是,有一个我绝对不会放弃的东西,一直在,绝对不会放弃,就是要做到让我妈妈在天堂看到,也会觉得很喜欢,会说,你看,那就是我的孩子。
“来,我们拥抱吧。我希望你好,一切都好,这是我的祝福。”??
声明:以上内容为本网站转自其它媒体,相关信息仅为传递更多企业信息之目的,不代表本网观点,亦不代表本网站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。投资有风险,需谨慎。